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中,还是在影视剧里,吴敬中(或称景中),军统特训班的高级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的站长,都是个令人畏惧的人物。曾在军统局担任过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及中将游击司令的某些高层领导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他,描述他资历深厚、能力出众、办事果断。而且,号称“叛徒”的他,能够在戴笠的领导下从军统局混到少将军衔,在局内也算是凤毛麟角,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然而,所谓“叛徒”的称号需要打个引号。因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曾经出卖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而且当时阵营的转换并不违背任何规则。就比如军统局的最后一任局长(也是保密局的首任局长)郑介民和蒋中正的儿子蒋建丰,都是吴敬中的同学,建丰甚至娶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妻子,还公开批评其父抛妻弃子,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郑介民的晋升,也没影响建丰的仕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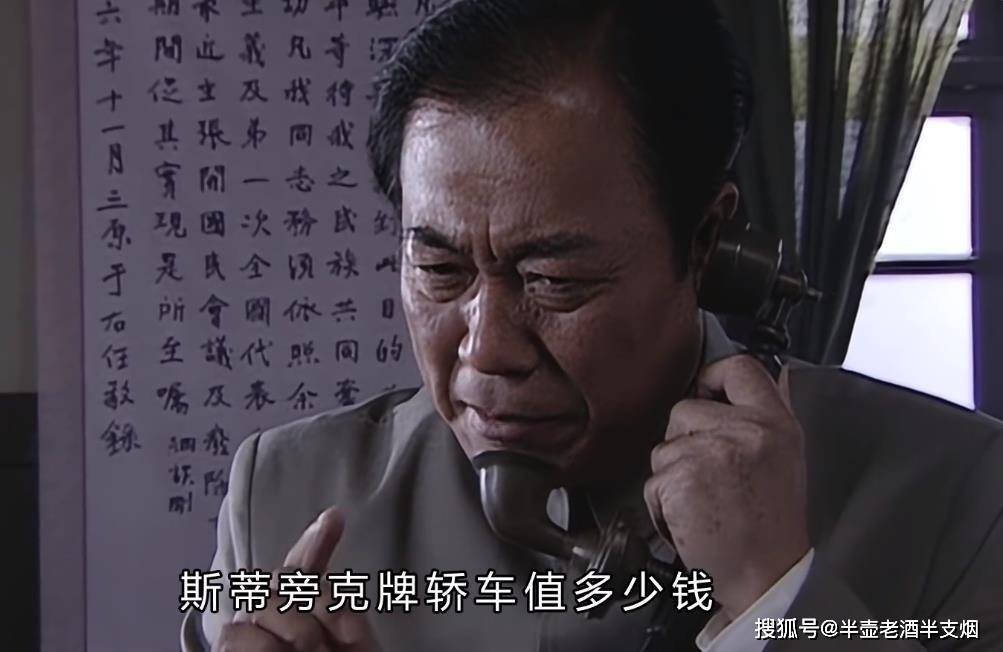
戴笠的正式军衔不过是少将(他挂的两颗星代表的是军统局副局长的职务军衔),吴敬中和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文强都获得了少将军衔,这也反映出他们的非凡身份与地位。

文强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被称作刘安国,这个人性格难以改变,所以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如果吴敬中走进功德林,估计不会像文强那样倔强,反倒可能像王耀武一样顺应环境,开始了新的生活。或许他会和沈醉一样,在1960年就开始过新的日子。

吴敬中智谋深远,透彻地理解世事并时常带着幽默感。他的回忆录必定比沈醉的更引人入胜——幽默本就是智慧的体现,擅长冷幽默的吴敬中,常常让人觉得他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他的刀冷得刺骨,他的剑冷得让人胆寒,他的血冷得像冰,他的心更是冰冷如霜。”
其实吴敬中并没有冷血无情,他之所以显得心灰意冷,更多是因为他对蒋中正集团的深刻洞察。在他眼里,所谓的“凝聚意志保卫领袖”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口号,真正的动机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蒋家、宋家、孔家、陈家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的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曾经问过余则成这个问题,大家心知肚明,革命不过是为了钱而已。

吴敬中很清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为那些特权,谁会愿意当官?”他的理念与“万里寻封侯”异曲同工,转换阵营的目的也是为了能从中获得更多财富。谁敢阻碍他的财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压谁。马奎、陆桥山、李涯这些人如果没有太大的威胁,或许还能幸免,但若稍有威胁,吴敬中必定会先发制人。翠平和廖三民如果没提前动手,吴敬中最终也会让保密局天津站的这三位中校无法善终。
虽然马奎和吴敬中并非同一阵营,余则成和他也有所不同,但为什么吴敬中对他们下手,却偏偏对余则成宽容呢?如果我们仅仅从利益和师生情谊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就太低估了吴敬中的聪明。事实上,吴敬中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信任,除了他的妻子梅姐。而余则成策划将斯蒂庞克的轿车换成金条和美钞时,吴敬中甚至特意向梅姐询问那辆车的价值,可见他对于余则成的担忧。
李涯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吴敬中财富的威胁,吴敬中设下计谋让李涯成为陆桥山遇刺案的主要嫌疑人。没有吴敬中拖住李涯,余则成根本不可能从小特务口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吴敬中之所以帮助余则成,是想在李涯身上套上一根随时可以收紧的绳索。陆桥山的死,李涯的手下被抓,余则成的证词将把李涯描绘成幕后主使,而这些证词早已是吴敬中一手安排的。
吴敬中并不只是让李涯成为替罪羊,对马奎、陆桥山也没有任何手软。吴敬中善于利用别人,利用陆桥山来对付马奎,利用李涯来对付陆桥山。而余则成虽然有价值,但也不是免死金牌,最终吴敬中对他还是采取了行动。余则成面对几个冷酷的彪形大汉时,竟然一个个都不认识。马奎、陆桥山、李涯一个个落网,连档案股股长盛乡也死在李涯的枪下,吴敬中自然早已知道,背后操控这些人的,是更大的权力。
面对最大危机时,吴敬中知道,余则成留在天津负责“黄雀计划”,一旦天津解放,余则成必定会暴露身份,届时他就会是吴敬中的敌人。为了保命,吴敬中必须掌握余则成的动向。即便余则成能力出众,但在吴敬中的眼里,随时准备“下手”也并不为过。对于吴敬中来说,除了妻子梅姐,余则成再也没有任何可信之人。
当余则成不顾吴敬中的意图,开始推动“黄雀计划”时,吴敬中冷冷地问道:“你又要留下来?”余则成机智地转变口风,立刻说:“我听您的吩咐!”这让吴敬中并未如以往一样露出笑容,而是冷冷地指示:“你去查查那个给廖三民打电话的人。”

吴敬中把余则成推向调查的深渊,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查出真相——电话交换机能迅速揭示谁与谁通话。吴敬中并没有干涉余则成调查的结果,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吴敬中早有自己的计划,他的影子部队很快就找到了余则成的住所。

三个冷面特工出现在余则成面前,一字排开,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只是命令他交出武器。余则成虽然迟疑,但最终放下了枪。按理说,余则成身为中校特工,应当没有理由交出武器,但这次是吴敬中亲自指派的行动,意味着吴敬中已经在试探余则成的底线。如果余则成拔枪相向,那结局注定不会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