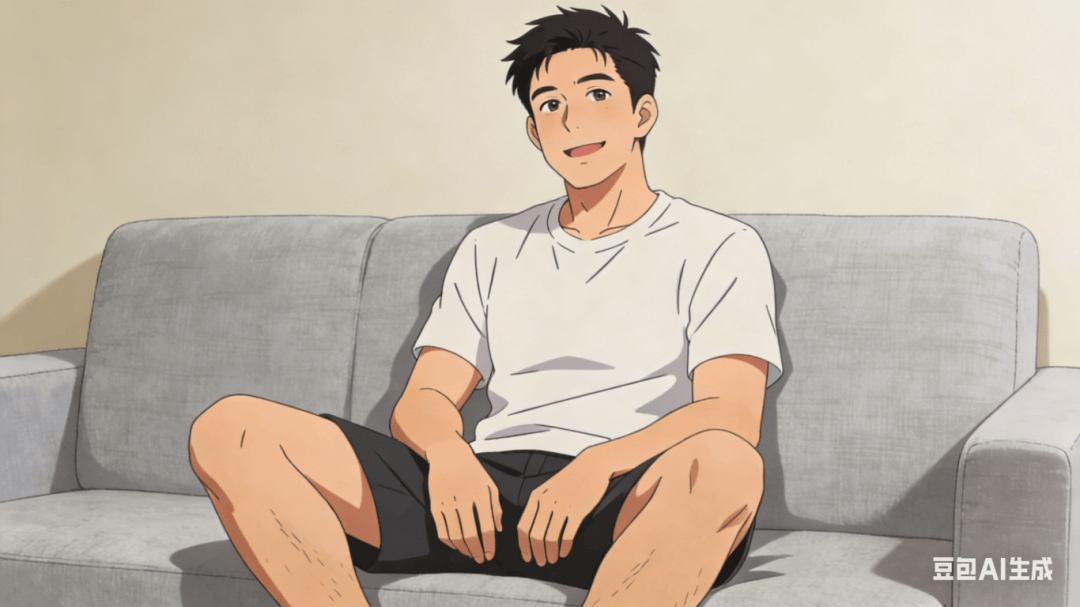阿琪告诉我她的咨询目标:“讲话流畅,不结巴。”说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这个女孩剪着干净清爽的短发,却有着害羞又闪烁的眼神。

“阿琪,你的咨询目标是讲话流畅,不结巴,能具体讲讲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老觉得自己讲话不流畅,尤其是在某些时候。前两周我去姐姐姐夫家,一进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话都说不出来,有时候在宿舍里也是这样,明明想好了怎么讲得,却老是有卡壳的感觉。”阿琪断断续续地说,一边努力在往下咽着什么。
在阿琪的印象里,这种“结巴”从初中时就开始了,上了大学之后有时好些,有时又变得更严重,她觉得自己表达能力很差,说话又结巴,很担心这会影响到她未来找工作。“就是感觉自己讲得好好的,一下子卡住了,越急越讲不出来,自己又笨又傻的,我在公众场合很少讲话,朋友聚会时也怕出现这种结巴,丢人死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在阿琪和我交谈的前二十分钟里,没有所谓的“结巴”,阿琪讲话有些断断续续,但只是停顿,有时她会有要把话咽下去的动作,但不是阿琪自我评价的表达能力很差,说话又结巴,这种缺陷会影响到她找工作。

我于是直接对阿琪说:“阿琪,其实你若不告诉我你说话结巴,会卡住,在和你交谈的这段时间里,我可真是一点都听不出来。但是这种感觉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你能说说看,上一次你自己觉得卡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
“上一次严重的就是去姐姐姐夫家,我一进门想要叫姐姐姐夫,居然卡住了,结结巴巴的,觉得自己特别傻。”阿琪皱着眉头说,“昨天在宿舍里也是,我舍友用了我的热水瓶,冬天那么冷,我自己打的热水是准备晚上洗漱用的,她招呼也不打就全用掉了,我想说点什么,但又卡住了,自己站在那里纠结了半天,觉得特别笨,话都说不出来。”阿琪说到这里,咽口水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阿琪,你能体会下自己此刻的感觉吗?当你咽口水的时候?”
“觉得胸口很堵。”阿琪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
“可以详细描述这种胸口堵的感觉吗?让我也可以体会到?”
“就好像有很多碎碎的石头压着这里,喘不过气,得大口呼吸。”
“好像还有什么要继续压着,不让石头冒出来?”
“是,在嗓子这里,好像有个井盖子。”
“黑色的,很重很重。”阿琪喃喃地说。
“觉得压得很辛苦,这个井盖压得很辛苦。”
“对,要很费力地压住,而且井盖要时刻保持警惕,碎石头好像随时可能沸腾。”我也试着体会阿琪的感觉。
记忆重组轻轻贴近那些固化的负面想法与情感模式时,没有急促的转动,也没有蛮力的撬动,只是缓缓地、一点点地施力。那些盘踞心头许久的陈旧情感循环,就在这温柔的力量中慢慢松动、逐渐瓦解,像冰封的河面在春日里悄悄融化,没有剧烈的碎裂,只有无声的消融。
而随着这些固化模式的松动,积压了不知多久的负面情绪,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口。不再是憋在心底、翻涌难耐的委屈,不再是压在胸口、喘不过气的烦躁,而是顺着这把钥匙打开的通道,像山间清泉般自然流淌,像微风拂过般平缓释放。心灵卸下了沉甸甸的包袱,重新找回了轻盈自在的状态,仿佛能随着风轻轻舒展。
阿琪大声地喊出来,眼角都是泪水。过了一会儿,她喃喃地说:“井盖,好像是刚才松动了,变轻了,没那么沉重了。”
似乎阿琪所谓的“结巴”其实和她不允许自己表达愤怒有关,而这种冲突在身体的感觉里好像成了“碎石头”和“井盖”,一旦阿琪让井盖变轻,碎石头可以冒气,这种所谓的“结巴”也就不需要了。
在接下来两个月的干预里,阿琪和我谈论的主题从她对舍友无法说出口的话,逐渐过渡到她对姐姐的愤怒与愧疚。原来,阿琪从小父母离异,姐姐对她来说相当于母亲,一直照顾阿琪的饮食起居,可是姐姐的确又像这位舍友一样习惯地不尊重阿琪的意见,让她有很多无法言说的愤怒和无助。一旦阿琪能够注意到自己不允许表达的情绪,注意到这份强烈的愧疚,在日常生活里,这种奇怪的卡壳逐渐减少了。

每次咨询时,我都会和阿琪一起进行场景重建干预,用正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在阿琪离开咨询室的时候,井盖已经很自然地变成了可以控制打开、关闭的水龙头,碎石头也变成了淡蓝色的湖水。阿琪说:“站在湖边,觉得宁静、舒适,但我还是需要一个水龙头,有时打开,有时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