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占全球总人口的13%,然而,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深陷于病耻感,羞于向任何人乃至医生提及此事,他们不仅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被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污名压得喘不过气。
如何破除对精神疾病的误解?译林出版社“医学人文丛书”第14册《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前主席杰弗里·A.利伯曼,而APA正是被全球精神病院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奉为圭臬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制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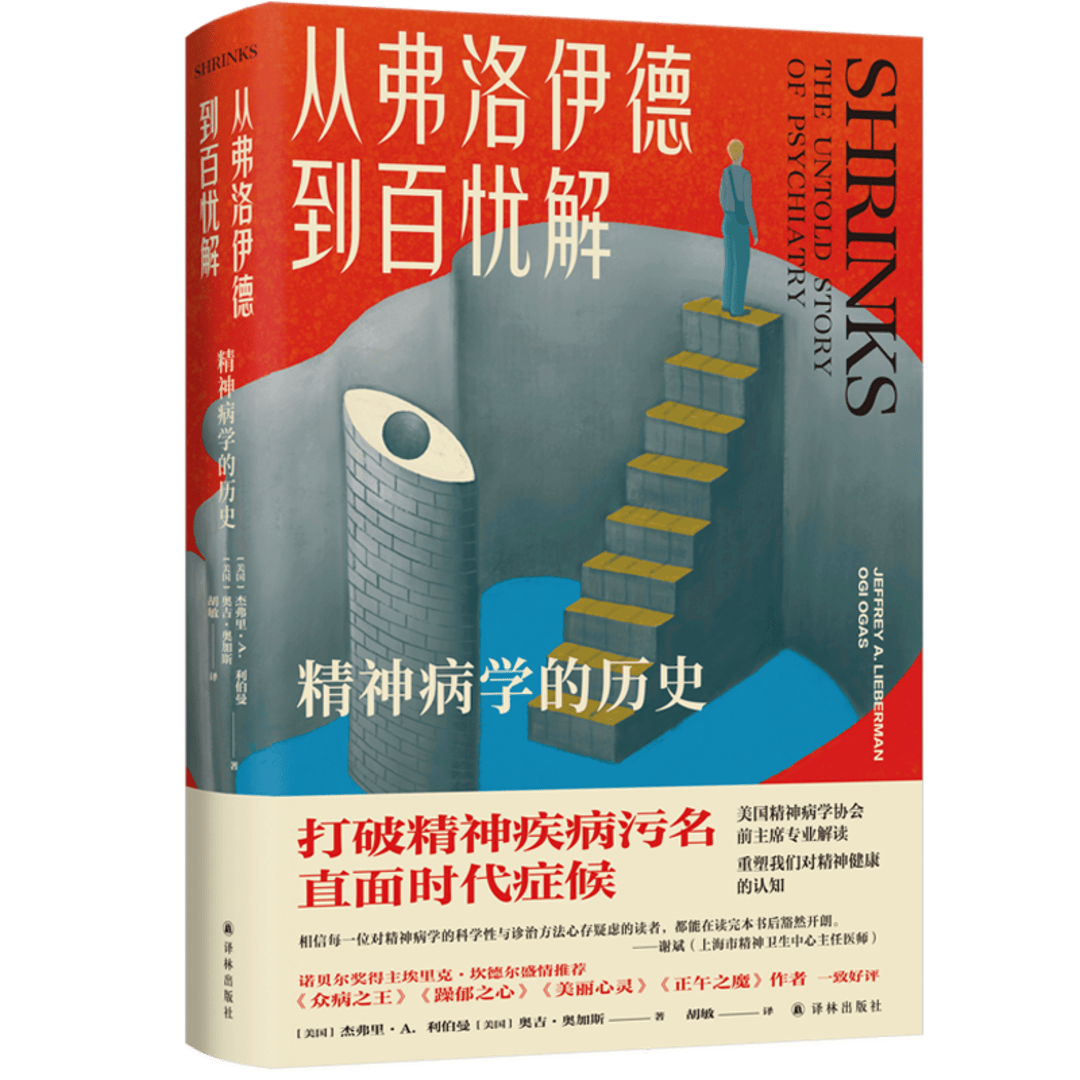
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症状与正常情绪的界限十分模糊,病因又无迹可寻,而科学又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在大脑研究上取得突破,精神病学早期荒诞无稽的“黑历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历史上第一位精神科医生是威廉·赖希,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生命能”学说,认为精神疾病源于患者体内的生命能阻塞。他自制了“生命能蓄能器”用于治疗——让患者挤进一个电话亭大小的箱子,在其脖子上挂一根橡胶软管。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荒诞的学说不仅吸引了大批患者,还获得了主流医学期刊的认可。
像这样近乎骗术、毫无疗效的学说还有很多,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把患者固定在椅子上,然后将其旋转,用鸟笼一样的盒子罩住患者的头,隔绝视觉和听觉,还给患者开用水银做成的强力泻药。葡萄牙神经科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发明了脑白质切除术:在病人的颅骨上开孔,将器械伸进大脑,像挖苹果核一样挖取脑组织,他还因此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利伯曼毫不回避这些让从业者蒙羞的过往,但他也提醒我们:精神病学一直在“大脑”和“心灵”之间摇摆,这导致早期的精神科医生既渴望科学,又难以逃脱奇想与怪谈;那些近乎虐待的疗法,其初衷都是为了救人。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开创了治疗师与患者通过谈话达到治愈目的的模式,为心理治疗制定了基本规则,此后精神分析一直在谈话疗法中独占鳌头,直到认知行为疗法(CBT)横空出世。
行医多年的利伯曼感叹道:“作为一名既有临床护理一线经验又有精神病学前沿研究经历的医生,我目睹了势如破竹的进步改变了精神病学……但不幸的是,不是人人都能从中受益。……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
他遇到过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被家人关在别墅里的现实版“阁楼上的疯女人”,因为感到丢人而迟迟不肯将女儿送医的社会名流……精神病学好不容易在大脑和心灵的天平上取得平衡,兼采生物学派和心理动力学派之长,但却卡在了让病人愿意走进精神科挂个号这一关上。
要解决这个难题,答案不在医院内,而在社会中。只有破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消弭社会对患者的污名,那些躲在角落的受苦之人才会愿意走出家门,求医问药。而这一切,要从了解精神疾病的真相开始。这也正是利伯曼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谢斌在读完此书后评价:“相信每一位对精神病学的科学性与诊治方法心存疑虑的读者,都能在读完本书后豁然开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